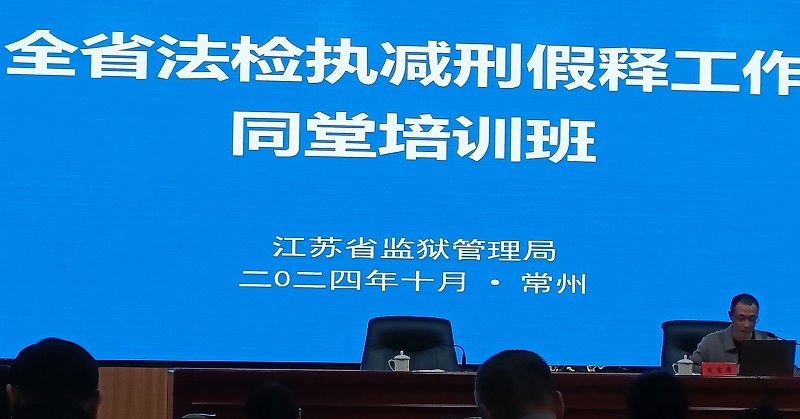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兴起,网络成了诈骗类犯罪的主战场。当前,网络诈骗具有作案手段多样,方式隐蔽、资金流向复杂等特点,证据体系更多的向电子证据倾斜。在对涉案电子数据鉴定过程中,全面、客观的提取和分析相关数据,获取有效的电子证据,对案件准确定性和精准量刑至关重要。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至今,犯罪嫌疑人钱某伙同他人注册成立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信息网络方式虚构事实、推销并销售并无疗效的增高产品,对数万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累计销售金额达六千余万元。
[案情难点]
诈骗类犯罪中,诈骗金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销售的产品种类多达百余种,其中部分如美白等产品的销售金额并不计入诈骗金额;同时,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其刑事责任,将其作案电脑硬盘数据库中客户订单中的金额进行了篡改。如需确定具体的诈骗金额,一方面需要提取订单未经篡改之前的原始数据,同时需要对相关数据中的产品订单逐一分析,获取有效的诈骗订单信息,从而才能确定具体的诈骗金额。侦查阶段,办案机关曾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对该硬盘数据库中的相关客户订单数据进行了提取,但其关注焦点仅在分析数据的真伪、是否经过篡改,而忽视了相关订单内部的具体细节信息,因此未能得到有效的作为该案关键证据的诈骗订单信息。
[鉴定经过]
为解决专门性问题、查明案件事实,办案检察官委托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数据进行了鉴定。
检察技术人员在电子数据实验室对涉案服务器进行了深度的扫描搜索,发现了五份完整的数据库备份文件、一份数据库缩小操作的SQL文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聊天记录证实了犯罪嫌疑人曾要求开发工程师将销售金额进行缩小的操作,工程师将相关操作SQL文件发送给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将数据库备份后执行了金额缩小操作。为进一步查明案件真相,检察技术人员又通过搭建数据库运行环境,恢复各个时间节点的数据库,结合案情,分析其中的订单数、金额、时间等属性,最终确定了一份未被篡改的数据。该案共涉及两万余条订单信息,但订单中有部分订单中的销售金额并不记入诈骗金额,检察技术人员遂通过分析数据库中的五十多份表格,发现了表格之间的联系,通过多表联合查询,分析出每种产品的金额,最终精准确定了诈骗金额,为该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案件启示]
网络诈骗案件中的诈骗方式、金额等与犯罪构成和定罪量刑有直接关系,这些数据均存储在网站的数据库中,只有全面、客观地收集、分析、提取、固定相关数据,才能有效发挥相关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
第一,电子数据取证过程应当更加审慎规范。网络诈骗案件中,作案用的服务器多数为网络虚拟服务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采取远程勘察手段获取系统代码和数据库,其中远程勘验报告、现场勘查笔录是证明数据库来源的重要证据,由于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存在技术差异,勘验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旦失败可能导致整个证据丢失,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整个勘验过程中,需要详细地记录电子物证的状态、位置、网络参数、在线分析过程等情况,确保提取、复制、制作过程规范,内容真实完整,与案件事实精密关联,使之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
第二,电子数据取证应全面挖掘、综合分析。电子数据取证时,分析数据的真伪固然重要,因为电子数据如系篡改、伪造,或者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客观、真实情形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在网络诈骗类案件中,作为关键电子数据的“数据库”是非常抽象的,在鉴定数据真伪的基础上,还需要围绕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用科学的方法从中提取出人数、金额等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电子数据,使得电子数据在案件中更好地发挥其优势证据的证明作用,而优势证据主要包括基于原始电子证据,经过科学分析后提取的电子证据或其它衍生证据,这些证据与案件联系紧密,可重新验证,不易变动,具有权威性。
第三,健全完善检察技术辅助办案协作配合机制。《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注重审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多元关联,加强综合分析,充分发挥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此条不仅仅是对检察官的审查要求,也是对检察技术人员电子取证工作的具体要求,电子数据能否成为关键或者优势证据,取决于电子数据取证是否客观、精准,取决于审查把关是否全面、到位,而电子取证可以说是“源头”环节。因此,检察技术人员在电子取证时,应当坚持办案导向、树牢办案思维,针对疑难复杂案件中的技术问题,主动邀请检察官参加案件讨论及技术会办,形成检察业务和技术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好电子数据取证等检察技术为办案提供证据和技术支持、监督纠错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