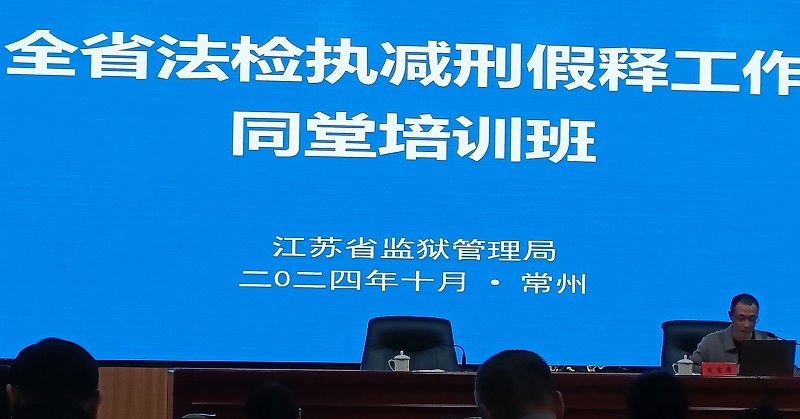吴华斌 王 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提供了价值引领。资源是自然的基础性要素,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可表现为生命要素(如植物、动物、微生物),发挥着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不同作用,也可表现为生命支持要素(如水、土地、矿藏),发挥着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民法典第1235条,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下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赔偿损失的主要标的是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分为生态服务功能修复期间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永久性损失两种类型。在诉请生态服务功能修复期间损失或生态服务功能永久性损失时,如果不明确涉案生态服务功能的具体内容,那么其诉请就可能千篇一律,体现不出不同类型案件的个性。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1部分:总纲》(2020年)在定义生态服务功能时,列举了四项内容: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功能。司法实践中,可以结合具体案情从上述四个方面具化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面,笔者以2023年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某非法开采泥炭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阐述具化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思路。
一是分析资源特质。该案违法行为人的作案目标是泥炭,因此,可从研究泥炭的自然属性着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咨询专家意见,了解泥炭的形成、特性、用途,分析提炼该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泥炭是地上沼泽植物的“遗体”腐化后,经过数千万年的堆积,在较低气温、缺少空气条件下,缓慢分解而形成的特殊有机物,含有大量水分和未被彻底分解的植物残体、腐殖质以及一部分矿物质,可以被用来制作肥料。泥炭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能够吸储超过其自身重量的水,因此也可以作为栽培基质用于园艺行业。违法行为人之所以采挖泥炭,正是受上述经济利益驱使。在自然状况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植物枯死后在沼泽的特殊环境下堆积形成泥炭,由此碳被长久地固定在泥炭湿地中。有学者撰文介绍,泥炭地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地之一,泥炭地仅占地球表面的3%,却保存了全球约30%的土壤碳储量。综上,可以将该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具化为固碳蓄水能力损失。
二是关注生态区位。该案案发地位于若尔盖湿地。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若尔盖湿地主要分布在四川的若尔盖县、红原县、阿坝县、松潘县以及甘肃的玛曲县、碌曲县部分区域。黄河流经若尔盖湿地,丰水期径流量增加29%,枯水期径流量增加40%,若尔盖湿地因此被誉为黄河上游“蓄水池”,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通过考虑生态区位,可以增强该案蓄水功能损失的内心确信。若尔盖湿地高寒缺氧,是典型的高原湿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凸显了当地野生动物的珍稀可贵,应当对其生存环境予以特殊关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08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案发地虽不属于若尔盖湿地核心保护区范围,但鉴于水禽的迁徙流动性,案发地依然具有提供水禽栖息地的服务价值。若尔盖湿地是黑鹳、金雕、玉带海雕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以及喜马拉雅旱獭、马麝、水獭等珍稀、濒危野生兽类的共同栖息地。通过考量以上因素,可以将该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具化为动物栖息地服务功能损失。
三是考察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所呈现的客观状态对认定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具有启发作用。放养牦牛是阿坝州藏族同胞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若尔盖湿地是重要的牦牛放牧区。有牧民反映,违法者盗挖泥炭后形成的坑洞在下雨后会有积水,有牦牛在觅食、迁徙时不慎跌落其间而被淹死。非法开采泥炭行为破坏了地貌导致动物过境受到影响,降低了生态连通性。通过考察该案案发现场,可以增强动物栖息地服务功能损失的内心确信。此外,案发地红原县、若尔盖县自然景观丰富,对于当地来说,维护景观多样性、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既有生态、美学价值,也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该案盗挖泥炭行为导致1560.48平方米草场遭到破坏,损害了当地一定规模的草甸景观。俯瞰或远望涉案地块,盗挖泥炭后留下的坑洞与周围自然环境极不协调,形成不佳观感。因此,还可以将该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具化为景观多样性损失。
遵循上述思路,认定该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为:固碳蓄水能力损失、动物栖息地服务功能损失、景观多样性损失。该案被盗挖泥炭已被行为人售卖、无法追回,而泥炭的形成需要历经漫长岁月,基本上不可再生,因此可将固碳蓄水能力损失归结为生态服务功能永久性损失。对盗挖泥炭后留下的坑洞,可以通过回填他土、恢复植被覆盖修复地貌,因此可将动物栖息地服务功能损失、景观多样性损失归结为生态服务功能修复期间损失。固碳蓄水、动物栖息地、景观多样性分别对应生态环境的调节服务、支持功能和文化服务。
对于已经具化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在缺少量化损失鉴定方法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开听证、专家论证等方式酌情确定损失数额,实践中也已有相关判例。从最高人民法院第207号指导性案例(2022年)——“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来看,该案虽然可以认定非法采矿行为造成山体破坏和植被毁坏,导致哺乳动物过境受到严重影响,但因没有相关研究依据而无法量化计算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功能损失。对于此类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金额难以量化计算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专家意见,综合考虑涉案区域植被覆盖率、所在位置以及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影响等因素,提出按照案中其他可以量化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总额的1%酌定计算的意见,该部分诉讼请求最后得到了法院判决支持。
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十分依赖鉴定意见,它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鉴定意见、评估报告、专家意见的功能只是帮助检察官或法官更好地认定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并不能完全替代检察官、法官履行司法职责。鉴定评估等技术判断只是认定事实的辅助性手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法律原则、规则指导下的价值判断,即司法判断。强化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司法判断,一要加强法律规范、司法解释与技术标准的衔接,除了直接在法律规范、司法解释中加入技术标准的相关内容,还可以通过设置“准据”条款,以转介方式引导法律规范、司法解释与技术标准建立联系,发挥技术标准的工具性作用,解决法律适用中的技术性问题,促使法律规范、司法解释与技术标准从分散走向融合、从各行其是走向协调一致;二要增强司法人员生态环境领域专门性知识储备,加强学习与办案有关的环境科学、生态学等方面知识,深刻理解、解读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以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自觉融合法律素养与环境素养,敏锐感知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的关联度,准确界定违法行为性质、程度,快速识别、判断涉案专门性问题,从而更好地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并综合审查确定鉴定意见及专家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必要时可以科学合理地酌情量化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