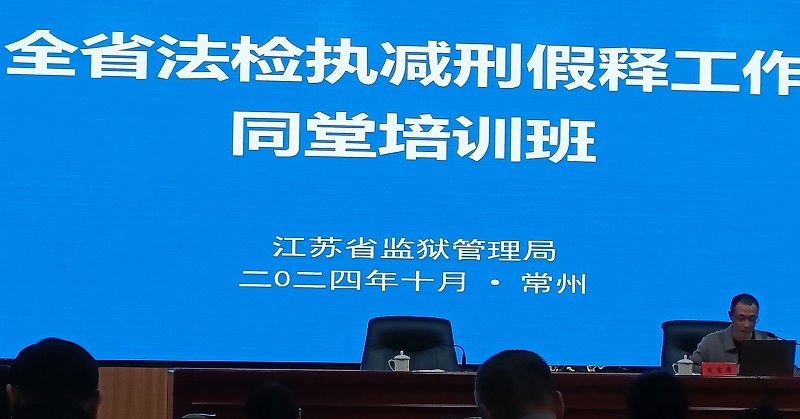恩施老城没有北京、西安等大地方的名气,却很有气势。老城的文化是被城墙圈起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店铺、客栈、茶肆、戏楼、书院、渡口、庙观、集市,目不暇接,颇有《清明上河图》的韵致,尽管后来城墙坍塌,沦为一片废墟,但骨架尚存,一些文化的元素散落在残留的青砖石碑上。五峰山上的宝塔,成为恩施老城的符号,六角亭、城楼、洗马池、关公庙等远去的遗迹,显示着那段历史曾经的辉煌。庭院天井,一地蔷薇,一洼积水映照着清冷的残月,留下故人远去的絮语和羁旅人的一抹乡愁。
叽叽喳喳的麻雀是老城的声音符号,夜晚用电筒在屋檐里找麻雀窝是孩子们的游戏。老城里的麻雀与人朝夕相伴,胆子大到可以与人在饭桌上争食,“城墙上的麻雀被吓大了胆”成为老城的名句。当天空中的雀声被飞机的轰鸣声取代的时候,高楼大厦旁的老城也开始变得萧条,古城墙上的蒿草在秋风中簌簌抖动。涌现出来的电视墙、超市、酒吧、广场、公园等一些现代时尚的元素,让老城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土布草鞋走向了西装革履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在母胎里就开始孕育的乡音,并将这种文化基因根植于血脉,随着探寻的脚步融进了大江南北。与外地交流,恩施“彩普”派上用场,但也闹出不少类似“买幺裤(短裤)”的笑话。人在他乡,无依无靠,偶听一句“您(列儿)快点来吃饭撒”,心中不免一热……
在老城人的眼里,嫩嫩的豆腐花上拌着佐料、撒上翠绿的葱花,咬上刚出锅的流着油汁的水浸包子,油锅炒菜发出的嗤嗤的声响,赶马车的把式扬鞭甩个脆儿……都是文化。人们从小就开始在这种街巷文化里浸泡,接受着这种启蒙教育,潜移默化,根深蒂固。无论如何包装,恩施人的土气难移,土得实在,土得可爱。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饥饿成为普遍感受,吃是一种向往,全部的幸福似乎都在一碗油炒饭上。老城里有句耳熟能详的问候语叫“你吃了没有?”有时甚至上厕所也没有忘掉这种“礼节”,时时体现出彼此间对温饱问题的关心和担忧。油水寡了吃什么都香。如果能够跷起二郎腿,在馆子里吃上一碗青椒肉丝面,用皮蛋蘸点蒜泥和酱油什么的,喝点苞谷酒,泡杯浓茶,然后打着饱嗝到戏院和电影院听戏看电影,那种惬意最令人羡慕了。
我感受老城的文化是从锣鼓声中开始的。小时候门前的街道时常走过迎亲送葬的队伍,里面有打花锣鼓的,他们多是穿蓝布对襟长衫的老人,头扎着蓝帕,熟练且严谨地驾驭几百年传下来的红白韵律,鼓点和唢呐以及锣声恰到好处的浑然一体,抑扬顿挫,烘托着喜庆和哀伤的气氛。我想起了作家陈忠实在《漕渠三月三》里描写的一位两腮凹进牙槽的精瘦老头握着鼓槌儿打鼓的情景,眼前这些打锣鼓的老人,和这位精瘦老头颇有些相似,他们陶醉在这种敲击和抚慰里,人们也乐于接受这种铿锵而缠绵的韵律,因为这是老城的艺术,是老城人的文化。
老城有唱戏的传统,戏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轮番出场,渲染着老城的“古”味。万家灯火之时,远远传来二胡悠扬的练习声,在城墙以及层层叠叠的瓦屋上弥漫,让夜空显得很深很静,透出一种雅致情趣。此时围绕老城流淌的清江,在月色下晶莹如银,闪烁着迷人的梦境。
舞龙是老城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到了春节灯会时节,各条街道上的舞龙队都汇集在一起,在热烈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演绎着“群龙会”。舞龙的小伙子们,个个不示弱,硬是把一条条龙舞得活灵活现,似腾云驾雾般飞向天空。这是老城人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刻,他们把一年所有的祝福和希冀,都寄托腾飞的彩龙上。
这样的老城,在锣鼓、二胡的音乐声中怎能没有丰富的语言,雕花的门窗印满了这种文化的精致。城门洞口剃头匠给人刮光头的风景已经远去,蚊香树上的知了也停止了鸣唱,老城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不论你走多远,她总是让你梦萦魂绕,这就是老城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厚重和魅力,不仅仅是一块块青砖石板垒砌起来的历史沉淀,早已融进了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转自江苏检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