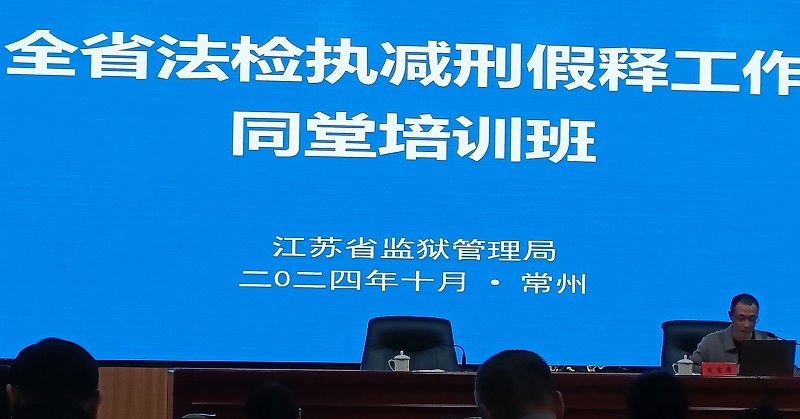路过一个小村子,远远地看到一个踮着小脚的婆婆,在前面的路口一拐就不见了,和我多少次梦见的场景竟然一模一样。尽管老婆婆没有回头,我还是认出了她。是的,不会错的——那样瘦小的身子、那样颠簸的小脚、那样雪白的头发,不是外祖母还能是谁呢?
可是我知道,我这样言辞灼灼的推辩,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外祖母已经离世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亲戚们很少谈起她。不是不想,而是因为谈起来只能徒增悲伤。有一次,我母亲对我四姨说她常常会梦见外祖母,四姨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已是满面泪痕,她说,她也总是梦见,她说,梦中她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想拉紧自己母亲的手,却怎么也触不到那厚厚的皱纹。
这一年里,我曾无数次想提笔向自己也向别人讲述外祖母坎坷而平实的一生,又无数次将手中的笔抛下。我实在不知从何处说起,我对她的了解太浅薄了,浅薄得让我脸红耳臊。我只知道,外祖母一生一共生下了母亲兄妹八个,其中的一个只瞧见一眼那个饥饿的年代,就已经夭折;我只知道,母亲是她最小的孩子,生下她的时候外祖母已经快五十岁了;我只知道,自打我记事起,外祖母就已经很老了……
我只记得,父亲、母亲下地去干活,很晚了还没有回家,只有外祖母搂着我,给我讲穷小子娶上漂亮的天女的故事。外祖母一次次地将我揽在怀里,唤着我的乳名对我说,你可要快点长大啊,长大了要快点结婚,姥姥去吃你的大馒头。多少年之后,我依旧是个穷小子,故事里的天女还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而外祖母却已经不见了。
我只记得,那个放了学的孩子,在野地里玩累了之后,半路上悄悄飞进外祖母的草房子里,从外祖母的手中接过扣在一起的饭碗,毫不客气地将里面的瘦肉吃个精光,抹抹嘴角,摸摸肚子,然后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背起书包大摇大摆地往家里走。多少年之后,我去过很多地方,吃过很多美食,却再也没有品尝到像外祖母为我留下的瘦肉那样好吃的东西。
我只记得,在无数个夜晚,有一个满脸黑乎乎的孩子,挑着外祖母扎制的小灯笼,沿着纤细的小路,从邻村一路小跑着回家,跟在后面的外祖母,踮着小脚、喘着粗气,一直目送着那孩子跑进自己的村子,才回过头,一步步向回走。多少年之后,我孤零零地跪在外祖母的灵前,眼望着棺材前方的那盏长明灯,想起了那些在小路上跳动的纸灯笼——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天又要黑了,可是,我该怎么回家?
外祖母在世时,我总想着要多孝敬她老人家,却又总找借口说,以后的机会多着呢,过一阵子再说吧。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外祖母再也熬不住了——一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外祖母毫无预兆地走了,享年九十二岁。那天晚上,外祖母逝世的消息传来,我狠狠地抽了一包烟,一句话都没有说。外祖母的葬礼上,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浩浩荡荡地从不同的村庄和姓氏里出发,赶往那个名叫黄家馆的小村子,来看她最后一眼。那天的某个瞬间,我的眼睛掠过表哥、表姐们悲伤的面容,定格在外祖母干草似的瘦小的身体上,我在想,也许这就是她的一生了。
外祖母走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她还活着,就活在我朝夕与共的生活里,和往常一样,几乎每天都可以遇见她老人家。可残忍的现实却不容我沉浸在往日美好、恬静的日子里,它一次次地告诉我,逝去的已经逝去,我只能往前走。她去世后,轻飘飘的一生就葬在院外的那片空地里,和多年前离世的外祖父躺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从路上走过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向着院墙下张望,随后才想起,外祖母早已挪动了位置。再抬眼向另一个地方望去,才发现,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外祖母的坟上已经是荒草离离。
有一次,母亲坐在堂屋门前给我缝补着衣服对我念叨着说,快到外祖母的周年忌日了,要准备些去上坟的东西。我猛然想起好几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满头白发的外祖母坐在暖阳下,为我的母亲拔白发。外祖母的眼睛早就花了,手也颤巍巍的,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根白发。每拔下一根白发,外祖母都要惊慌地喊一声,呀,拔错了,是根黑发,然后将白发偷偷藏到自己的口袋里。那一年,外祖母已经年近九十了,母亲也快五十岁了吧。
一转眼,又几年过去了,外祖母已然仙逝多年了,而我的母亲,头上也早已落满了白发,再怎么拔都拔不干净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检察院)
转自江苏检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