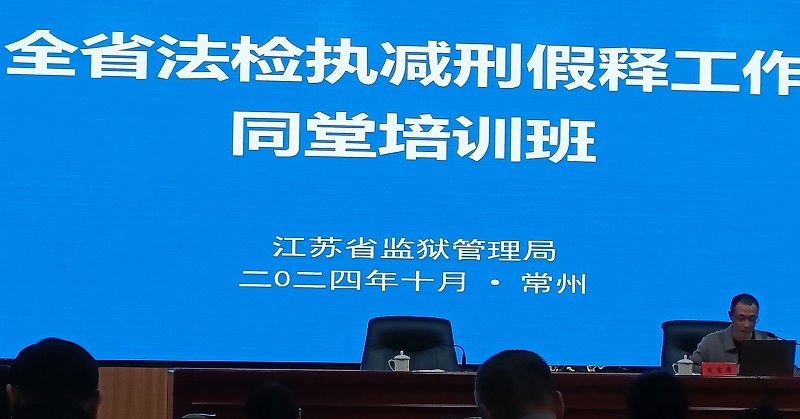1.公民个人信息应当有载体予以记录,且电子载体是重要表现方式。公民个人信息有载体是国际法律的共识。这是因为可搜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才有价值,而没有载体记录的公民个人信息无法搜集,侵犯此类信息也有可能对公民及社会产生伤害,但其伤害性往往较小且难以衡量。故无载体的公民个人信息一般不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2.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具有身份识别性,即无论是单独还是多个信息结合后能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都应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本身并不一定能指向特定自然人,但电话号码与地址、工作单位等信息结合在一起后,即有可能指向特定自然人,这种信息也应当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
3.公民个人信息不限于传统的身份信息,反映公民活动状态的信息也应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传统的公民个人信息往往只包括姓名、住址、电话等常规内容,而现代智能设备的发展给公民信息附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在传统互联网用户大量使用智能手机、平板设备后,近年来,可穿戴设备的使用率也日益增多。常见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包括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这些智能设备往往会暴露公民行动轨迹等非传统信息。而现代社会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商业行为等往往针对的就是此类信息。
(二)个人信息的属性及利益衡量
1.人格权属性。个人信息可以识别个人身份及活动情况,其人格权属性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所挖掘的个人信息内容已经涵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期的表象数据(姓名、住址、电话)到如今的内在数据(个人偏好、个人需求);从早期的静态数据到如今的动态数据(运行轨迹、位置信息)。
2.经济属性。个人信息具有经济属性是勿用置疑的,个人信息会产生不可小觑的财产型利益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同时应当看到,虽然公民个人信息的经济属性成为犯罪多发的诱因,但其也是促进商业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合理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
3.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利益衡量。从个人信息的属性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利益衡量。由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其作为人身基本权利,应当受到较为全面、完善的保护。
三、大数据发展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利益平衡
如何调和大数据发展对数据需求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统筹兼顾略有侧重的基本原则,即首要考虑公民个人信息的人身权属性,同时兼顾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体来说,大数据时代我国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内容:
1.合理配置纳入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刑法调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全面、合理。从《解释》来看,我国刑法所处理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仅包括提供、购买、出售、收受、交换等行为。而实践中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更为复杂,常见的包括修改、删除、检索、比对等一系列行为均没有规定,这必将不利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中的敏感信息如何保护也没有具体规定。如涉及未成年信息、个人医疗信息。
当然从信息化社会发展需求来看,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也不能过广,否则不符合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禁锢信息发展速度。具体来说,应当形成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和宪法保护、行政法保护、民法保护的良性体系,对于严重影响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才需要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
2.法律规定应全面考虑大数据时代犯罪手段特征。如前文所述,大数据时代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手段复杂、传播速度快等特征,导致案件侦查、认定困难。因此立法者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考虑应当更加全面。如为更好地打击跨区域性的诈骗等案件,2011年4月两高与公安部、国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就将“犯罪行为发生地”扩展为被害人接到诈骗、敲诈勒索电话、短信息、电子邮件、信件、传真等犯罪信息的地方,以及犯罪行为持续发生的开始地、流转地、结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扩展为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的账户转账或存款的地方,以及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该意见提出了一个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思路,对于我们处理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也有极大的帮助。
3.充分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公民个人信息利用中的作用。综合来看,在公民个人信息利用中,公民、营利性组织(如公司)、政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解释》对于营利性组织在刑法规制中的角色没有充分的阐述,导致我们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还停留在传统的信息买卖这一层面上。而行政机关在这一方面已经走在前端,2017年9月24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联合公布了隐私条款专项工作评审结果。参与评审十家企业共同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倡议书》,对尊重用户知情权、控制权,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保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可信等做出承诺。参与评审的企业涉及到购物、出行、旅游等各个领域。这一政府行为即是对信息从业的营利性组织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而营利性组织对于个人信息损害的范围更广、手段更为复杂,有刑法调整之必要。研究营利性组织行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影响对于我们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