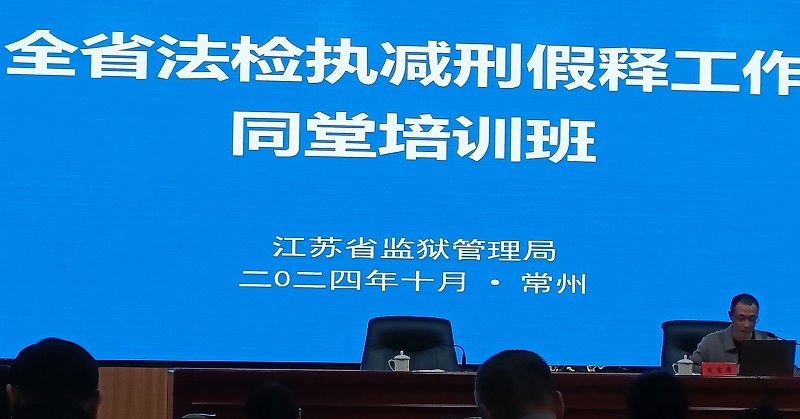胡思博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办理的养老保险领域系列虚假诉讼、虚假劳动仲裁检察监督案再次引发了笔者对虚假仲裁检察监督意义与方法的思考。
以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精神为基础的仲裁制度作为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以当事人的善意和诚信为前提。这使得仲裁相较于诉讼而言,更具自治性、合意性、秘密性、封闭性、灵活性、效率性等优势。但秘密性、封闭性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仲裁案外第三人知晓案情、主张权利,而自治性、合意性的优势也往往限制了案外第三人加入仲裁。近年来,具有合法外观与非法实质的虚假仲裁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双方当事人在形式上的对立性与实质利益上的一致性使得仲裁程序沦为被利用的工具,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极大损害仲裁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其危害和负面效应不容小觑。因此,检察机关对虚假仲裁开展监督,具有与开展虚假诉讼监督同等重要的意义,存在现实必要性。
对虚假仲裁开展检察监督可促进对非诉程序检察监督制度的全新构建,使非诉监督的理念和方式在诉讼监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如案外第三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能向检察机关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仲裁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检察机关可启动监督程序,通过向仲裁机构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仲裁机构再次对原纠纷进行以真实性判断为主要目的的审查。
就检察监督的启动而言,鉴于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处于联手串通状态,为此,案外第三人成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即启动检察监督的主要主体。
就检察监督的方式而言,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比较符合仲裁本身的准司法属性。这种方式是将对虚假仲裁存在与否的最终判断权交给仲裁机构,使仲裁机构的自我补救与检察监督相结合,检察机关并不作出根本性的事实认定和强制性的举措。
就检察监督的效力而言,仲裁机构采纳检察建议,对虚假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后予以撤销即体现了监督效果。笔者认为,应将仲裁机构撤销虚假仲裁裁决的事由另行单独明确,确立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构成虚假仲裁”,该仲裁裁决撤销事由既不属于程序性事由,也不属于实体性事由,而是判断仲裁合意成立与否的基础性事由。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